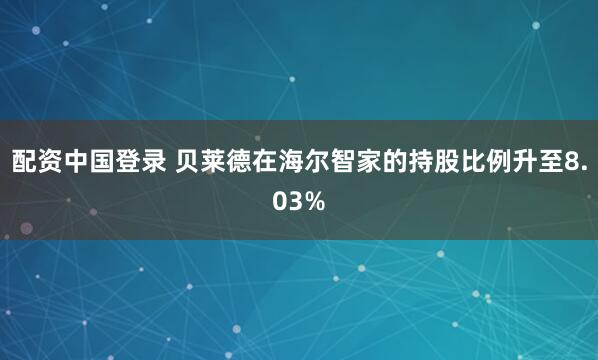“以前村里没这个厂的时候配资中国登录,村里人除了种田,日常就打打麻将打发时间。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工厂,空闲的时间大家都过来做伞。勤快一点的一个月能有四五千的额外收入,做得少的也有一两千。”

文 / 巴九灵
方佳骏的伞在拼多多卖爆单了。
“从年初到现在,我们伞的销量增长了大概有50%。”方佳骏翻着店铺的后台数据,盘算出了一个增长额。
他是拼多多平台黑标品牌“洋蜻蜓”的老板,主要销售伞具、防晒日用品。在网络上,他家的防晒伞是许多测评博主推荐的夏日防晒必备好物。
生意的暴涨,有气候的推动。夏至以来,高温席卷全国,从南部到东北一致陷入“炙烤模式”,漠河的气温甚至一度都攀升到了35摄氏度的高点。
高温撬动“防晒经济”。在“什么值得买”平台上,今年6月,“防暑”关键词商品GMV同比增长65.13%,防晒服配套面罩、袖套等GMV环比增长超40%。

高温下人们撑伞防晒
“从消费需求角度来讲,防晒伞是日用品,不存在什么特殊因素能推动40%、甚至50%的增长。”方佳骏坦言,“它的需求总归是有一个水平线可以去衡量的,多不了多少,少也少不了多少。”
这也意味着高温带来的需求增长并不足以支撑店铺销量的暴涨。
在方家骏心中,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有长久价值的作用不可忽视。
是增长,也是此消彼长
在复盘自家生意的情况时,方佳骏还有另一层面的观察,他发现在自家店铺销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过去一些依靠价格冲量、但质量存疑的同行店铺,今年的流量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不仅如此,平台的618大促、购物节等等购物活动,都没看见这些店铺参加的身影。”在电商从业人士看来,在平台的促销活动中,哪些店铺参与了、处在怎样的位置,都是反映平台流量倾向的重要观察点。
梳理下来,方佳骏店铺的增长背后,有承接同行店铺流量的因素在其中。
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在消费端来看,不显山,不露水,但身处其中的商家们,却对隐藏在变化背后的原因格外敏感。
“平台的游戏规则变了。”一位拼多多黑标店铺的运营负责人坦言,“以前很多商家在同质化竞争中找到的爆品单链逻辑,现在行不通了。”
“现在要看什么呢?”小巴问。
“要看你卖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今年以来,我个人感受到的是,平台明显加强了对商品质量的管控。”这位负责人强调说。
作为交叉印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拼多多商家向小巴描述了这种管控的具体细节。
“一方面,平台一旦检测到卖家有引导好评返现的行为,就会直接影响店铺的评分,并进而影响店家后续申请平台补贴、流量。另一方面,平台的工作人员还会私下下单买东西,拿到手去看商品质量等等一类的情况。这种线下的抽查,任何商家很难提前知道。”
“但如果真是好品质的商品,店铺就能得到平台的扶持。”多位拼多多的商家都告诉了小巴这样一条“游戏规则”。
商家表述中的扶持,即拼多多在今年4月推出的一项惠商计划——千亿扶持计划,从公开信息来看,这是一项涉及广泛、方式多样、持续时间长的惠商计划,但其核心目的就是通过资金、流量、技术等,为平台上的卖“好商品”的中小商家提供服务和支持。
乡村工厂正在赶制雨伞订单
从整个消费趋势来讲,拼多多的“千亿扶持”是顺势而为。
尽管在消费市场的叙事中,“消费降级”的论调不绝于耳。但从全球消费趋势变化来看,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消费升级依然是不可逆的总趋势,消费升级的一个具象表现即为:追求更高品质的商品。
上海消保委曾在今年2月发布过名为《好产品与消费新需求》的调查报告,受访对象达到6000人。报告揭露了一个事实,即更便宜的产品尽管能激发大部分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但同时却带来了消费者获得感的大幅度下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结论也再次印证了消费者对“好商品”的渴求。所以从消费端的需求变化来看,推动平台转变的要素已经充足。
而从商家角度而言,平台对“好商品”的强调,也是在催生一个更加公平、更加良性的经营环境。
方佳骏向小巴坦言,过去他们的生意常被同质化便宜商品拖累:“我们要把控质量,价格就没法跟那些劣质产品看齐。而在消费者更看重价格的逻辑下,大家自然就更愿意买那些便宜的商品。”
所以当平台游戏规则转向“好商品”,这些曾在同质化竞争中吃亏的品质商家,则成了第一波吃上红利的人。
“今年的生意能做成这样,我们心里确实挺满意的。”讲这句话时,方佳骏露出了腼腆的笑容,“平台扶持好质量产品的商家,消费者愿意买好的,商家赚到钱就有能力投入研发和提质。这是一种正向循环。”
如何做到好而不贵?
无论是被平台倾斜,还是消费者偏爱,方佳骏觉得商品能卖得好,除了“物美”,“价平”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创店到现在,过去六年时间里,我们在拼多多上卖出了六百多万的销量。店铺的复购率在18%,复购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0%。”
“行业的复购率一般在10%左右,”方佳骏进一步解释说,“从这些数据来看,客户对我们的商品满意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在装满货物的仓库里,方佳骏从纸箱里拿出了店铺的爆款防晒伞,这款防晒伞在拼多多上的定价是15元。
今年6月,这款防晒伞接受了一位叫@华肥娘娘的测评博主的测验。
博主将方佳骏店铺里的伞和网络上另一把售价超过百元的防晒伞做了防晒功能上的比较。
“平心而论,在骨架、制作工艺上,贵的伞确实比我们做的要好一些。但从测评结果来看,我们的伞和百元的伞在防晒这一硬性功能上,几乎不存在太大的差别。”
图源:小红书@华肥娘娘
所以如何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又能保证相对实惠的价格呢?
“一把卖价15块的防晒伞,各项生产成本7到8块,物流成本2块左右,运营成本两块左右,我们还能赚个两三块。我们直接生产、直接卖给消费者,也不打什么广告。甚至达人带货我们都不找。”方佳骏说。
在方佳骏的表述中,成本控制的账分为两本。
第一本是尽可能削减诸如推广、营销等带来的中间成本,源头生产、源头售卖给消费者。创业第一年,方佳俊店铺销售的还是找其他伞厂代工的商品,第二年他就建起了自己的工厂。
第二本账是降低生产成本。方佳骏老家在江西德兴,他在义乌租了一个仓库做分发中心,但产能却都放在了江西的村子里。
他最早的生产基地就是在自家村子的一栋平房里,开始只有十多个工人,都是自家的亲戚,一天能生产几百把伞。现在,这个基地的工人已经有八十多人,一天的产能在四五千左右。前两年,他又扩大了产能,建了另一个工厂,选址在江西宜春的另一个乡镇里。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考虑将产能全部集中到义乌这样的地方时,他的回答也很敞亮:“义乌这边物流成本低,所以我们将分发中心放在这里了。但这边的用地成本、人工成本却比我们老家那边贵了不少。”
之所以选择乡镇,图的是“地便宜,人便宜”。
这种“乡村生产+电商直连”的模式,在更广阔的乡土空间里正形成产业集群。
在德兴一千公里外的沧州青县,这座常住人口不足五十万的河北小县城,生产了国内市场50%的化妆刷,国外80%以上的高档化妆刷都产自于此。
这里的化妆刷工厂同样走着“物美价平”的路线——当地化妆刷的出厂价比同类城市工厂低20%—30%,通过拼多多直销,终端价仅为品牌货的一半,却能达到同等的毛质柔软度和上妆效果。
拼多多上销量第一的化妆刷品牌“魅女郎”的工厂,就坐落在青县北侧二十里屯村村口的一栋楼房里。
厂房流水线上做工的人,基本上都是村里的居民。根据当地居民介绍,过去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种田,而有了这些化妆刷工厂,当地人多了增收渠道。
沧州青县化妆刷生产
在青县,这样的工厂还有1000多家,从业人员约为1.6万人。数据对比而言,意味着其中绝大多数工厂都是小型甚至微型工厂。
这种小微工厂的生产模式在费孝通的文章中早有雏形。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就指出:在区别于福特式的现代工业生产之外,还可以推动现代工业分散下乡,他将其称之为“乡土工业”。
彼时在其论述中,就已经洞悉到了这种小微工厂的生产优势。他说:“乡土工业在经济上的优点却有都市工业所不易得到的。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是乡村工业中工资较低。维持同样的生活程度,乡村中所需的费用较都市里便宜。”
从现实情况来看,其理论价值放在今时今日仍不过时。同时,借助于电商生态带来的销售破壁,乡村工厂模式的成本优势则更加显著。
当任何一处的商品能通过电商平台,点击下单便能送往五湖四海,原本局限于地域的低成本生产能力,便跳过了层层分销的加价环节,直接转化为终端市场的价格竞争力。
从供需两端来讲,这一方面使得乡村工厂的利润空间能得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让消费者享受到了质优价平的商品,形成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双赢闭环。
乡村车间的兴起
从商家视角而言,将工厂放在乡村,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将选择放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视角来讨论,这种生产要素配置最大化的另一层作用是对乡村经济的利好。
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是一段放在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的高速增长史。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它也是一部乡土中国的失意史。
这种失意首先表现为人口流失。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已降至4.6亿,较2023年再减少122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约为32%,且这一数字仍在逐年下降。年轻人外出谋生,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乡村的肌理在人口流动中逐渐松弛。
乡村留守老人
乡村经济薄弱、就业机会匮乏,青壮年只能背井离乡谋生;收入差距拉大又让更多人选择离开,形成“人走业衰、业衰人更走”的循环。
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两者相差2.3倍。
所以如何增收、如何提供就业,是留住乡土中国的关键。
方佳骏在老家的工厂,吸纳了当地八十多人就业。
“以前村里没这个厂的时候,村里人除了种田,日常就打打麻将打发时间。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工厂,空闲的时间大家都过来做伞。勤快一点的一个月能有四五千的额外收入,做得少的也有一两千。”
“最重要的是,村里人喜欢就在家门口干活,你要是把厂搬到城里,他们也是不愿意去的。”
尽管缺乏全国性的数据统计,但我们仍可从局部的数据感受这种生产模式对乡村经济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截至7月6日,湖南省共有乡村车间6821个,吸纳就业人数超过33万人。
分散的乡村工厂一旦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带,那么除了直接生产带动的就业,还包括物流、客服、运营等全生态就业的增长。
以青县的化妆刷产业为例,青县的乡间工厂也已经从产业链,逐渐在向一个完备的产业带进阶。从“生产”到“产业链”再到“产业带”,其辐射更广,影响更深。
新“草根力量”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始终跳动着鲜活的草根脉搏。
温州模式,正是这种草根力量的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人用缝纫机踩出的纽扣、打火机,用锤子敲出的小五金,从家庭院落里的“前店后厂”起步,靠着“抱团走天下”的默契,把不起眼的小商品卖到了全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州工厂
时至今日,民营企业从“草根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了“树根经济”。
如今,电商平台上的中小商家,是这股草根力量在数字时代的延续。
从数据维度来看,这些中小商家对电商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2022年,亿欧智库就发布过一组数据:在今天的电商行业中,中小商家占比达到了80%以上。
但尽管如此,硬币的另一面却是中小商家在电商生态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电商增长的大部分红利由大品牌、平台获取。东方证券曾发布的一篇报告指出,头部商家GMV集中度高,有些平台30%—40%的GMV都由1%的头部商家贡献。
在过去,中小商家长期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平台流量多向大品牌、大企业倾斜,有直接生产能力的小微商家往往只能依附产业链上游:要么做代工,为品牌方生产却只赚微薄加工费;要么在价格竞争中压缩利润,难以积累资金打造自有品牌。
沧州化妆刷产业的发展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韩国企业看中了沧州的劳动力优势和地理优势,涌入此处投资建厂,吸纳了大量本地人就业,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生产流程,培养出大批技术工人。
这种就业模式属于附庸性质的被动生产,沧州当地工厂主要负责代工贴牌,处于全球产业链利润最微薄的一环,利润大部分被品牌方赚取。
后来,随着这些韩国企业撤出产能,沧州许多为韩企代工的工厂停产,众多工人失去工作,劳动力大量剩余,当地产业遭受重创。
所幸的是,一些工人凭借着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开始领办企业,尝试打造自主品牌,自产自营自销,也走出了一条产业振兴的路子。
沧州青县化妆刷工厂
所以自产自销自营,是沧州给出的将生产能力转化成市场话语权的解法。而在这种解法中,平台的支持和保护也尤为重要。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多集中在拼多多平台生态的讨论,其千亿计划是电商平台给予中小商家保护的一次具体行动,但从整个电商行业的发展来讲,行动不能,也不会止步于拼多多。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塔,起于累土。在无数中小商家为自己、为未来打拼之时,我们自然可以期待中国经济中又一个“树根力量”的生长。
本篇作者 | 田伟凤 |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配资中国登录
联合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